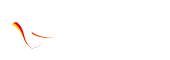物流巴巴訊,全球公共采購論壇發布的《中國采購發展報告(2014)》數據稱,2013年中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超過10萬億元,占GDP比重為18.0%,是美國8.5%的2倍多;在鐵路、高速等相對落后的印度,這一占比數據也僅有13%。在2014年,中國社會物流總費用同比2013年依然增長了6.9%。

這已經是全社會的共識。此前媒體已經多次報道過。但筆者發現,全社會對物流成本高問題的關注,僅僅局限在單位貨物物流費率高這一方面,而中國全社會物流量巨大的基礎背景,似乎沒人注意。而這其實才是造成物流成本在GDP比重過高的基礎因素。
比如,在國際貿易物流中,僅僅原料和能源類,我國每年需要進口7億噸鐵礦石、4億噸原油,3億噸煤炭,以及千萬噸級的液化天然氣。這樣巨大的進口量,在全世界幾乎都是第一。而出口產品運量規模,在各主要出口國中也名列前茅。
而在國內物流運輸中,我國貨物運量規模之大,更是各國望塵莫及。僅僅鐵路運量,每年約36億噸,遠遠超過美國的9億噸。其中僅煤炭一項就達到20億噸,而美國只有4億噸。公路、水路也幾乎都是如此。我國最大的貨物運輸品種是煤炭,年耗量已經達到36億噸,因為我國電力主要來源于燃煤發電。環保風暴也只能是控制煤炭消費的“過快增長”。而煤炭消耗,除去坑口電站就地消化轉為電力外,其余大部分需要直接運往消費地。巨大的貨運量,使我國單位GDP的運輸量遠遠高出發達國家,相應帶動運費成本在GDP中比例的高企。
而物流量巨大,是因為我國高能耗的重化工業和大進大出的加工工業的經濟結構。目前,中國經濟正在轉型升級調結構,中國制造正在朝著“中國智造”的目標脫胎換骨、鳳凰涅槃。技術含量越高的產業,對貨物運輸的需求就越小。
其中在電力消費方面,降低燃煤發電量,增加包括核電在內的清潔能源的比例,就能顯著降低煤炭運量;此外,即使是燃煤發電,增加坑口電站的比例,改輸煤為輸電,更是大量降低繁重污染的煤炭運輸。
在煤炭開發基地的布局上,應該盡量優先選擇靠近煤炭消費地的礦山。但目前國家將新疆納入新的開發基地,將面臨著漫長的運輸過程,這就與降低物流成本的訴求相抵牾了。
當然,運量大是基礎性的一方面;另一方面,單位運量費率高,也是突出問題。前一個因素扭轉起來時間可能漫長,而費率高這一個問題,則存在通過改革予以壓縮的空間。在各類高成本交通中,公路費率高的問題因牽涉面大而最突出,社會各界反應最為強烈。
目前,我國公路運輸費率僅次于航空。這固然有公路運輸自然成本高的因素,但更有我國特殊的公路過路費制度因素,以及油價高的因素。2011年新華社在一篇報道中舉過一個例子,1公斤貨物從上海到貴州通過公路運輸需花費6元到8元人民幣,而從上海通過海運到萬里之遙的紐約卻只需花費1.5元人民幣。雖然這個類比不是很恰當,因為在任何國家,公路費率必然高于海運、且不同貨種運費差別很大;但是,我國公路運費中,很大部分來自過路費,卻是不爭事實。比如,有快遞企業向媒體反映說,從上海到北京的公路運輸,跑一趟一天的成本就高達7000元。這中間包括車輛的折舊、駕駛員的工資、燃油費和過路費等。而油費和過路費所占的費用在這7000元中算是大頭,占60%-70%。
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此前做過一次市場調查指出,過路過橋費仍是物流企業沉重負擔,37%的企業過路過橋費占運輸成本比重超過40%,并呼吁撤并高速公路不合理收費站點。據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汪同三估算,全世界82%的收費公路在中國,流通成本占(物價的)50%-70%。不過,由于許多收費高速公路已經上市,取消過路費牽連到不少的利益方,阻力巨大。
需要壓縮收費的,還不僅是在運輸環節。同樣是《中國采購發展報告(2014)》的統計指出,運輸費用占社會物流總費用的比重為52.9%。也就是說,盡管運輸成本高,但在物流成本“貢獻率”中也只是占一半多一點,其余將近一半發生在其他等環節。這其他環節,相信應該包括倉儲,以及交易換手層次等。